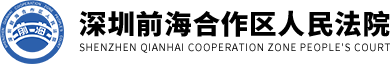关键词 隐名股东 解散公司
裁判要点 依照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有权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主体是公司股东,根据我国法理通说,这些规定中的“股东”的内涵是指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因此,原告作为被告宏美公司的隐名股东,没有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故不能提起公司解散之诉。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
案件索引
一审: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73号民事裁定书
基本案情
原告沈芬芳、叶伟光诉称:两原告是被告的实际出资人,案外人刘玉兰、潘永超是被告的名义股东。为确认原告系被告实际出资人的资格,原告诉至法院。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四初字第121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确认了原告系被告实际出资人的资格。(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已于2015年1月19日生效。原告在2006年7月6日以案外人刘玉兰、潘永超为股东注册设立了被告宏美公司。2008年底、2009年初开始,原告与作为名义股东的案外人刘玉兰、潘永超矛盾渐起且日益激化,终至原告失去对公司的支配权。为保护原告的权益,原告以刘玉兰、潘永超、宏美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以财产权属纠纷、股权纠纷、股权确认纠纷等案由多次提起诉讼,案号为(2009)深宝法民一初字第2698号(撤诉)、(2010)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948号(撤诉)、(2011)深宝法民四初字第121号(一审判决)、(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9号(二审判决)。(2011)深宝法民四初字第121号案件的一审、二审,对被告宏美公司、刘玉兰均为公告送达。被告宏美公司已于2010年1月停止经营。被告宏美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等仍在刘玉兰、潘永超控制中。原告与被告宏美公司名义股东刘玉兰、潘永超有关公司权益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被告宏美公司的继续存续将严重侵害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原告的权益。原告认为,被告宏美公司已经符合解散的条件。原告现诉请解散被告宏美公司,请求判令解散被告宏美公司。
经本院合法传唤,被告宏美公司、第三人刘玉兰、潘永超均未到庭答辩,亦未书面答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宏美公司于2006年7月6日成立,登记股东为刘玉兰、潘永超,分别出资比例为51%和49%。2015年1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确认两原告系被告宏美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裁判结果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73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沈芬芳、叶伟光的起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上述规定表明,有权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主体是股东,根据我国法理通说,这些规定中的“股东”的内涵是指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因此,原告作为被告宏美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是没有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的,故原告不能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综上,原告的起诉不适格,应予以驳回。
案例注解
本案涉及的问题是实际出资人,也即隐名股东的权利边界问题。实际出资人是指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并享有相应投资权益但不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的投资者,约定俗成称为隐名股东。通常情况下,股东隐名的目的是出于规避法律或者其他原因而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这里的“他人”即是相对应的显名股东。关于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与显名股东之间、其与公司外部债权人之间关系问题,在理论界存在各种学说,实务界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16日颁行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确立的处理原则是“双重标准,内外有别”。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的投资权益之间的纠纷,属于内部纠纷,依照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来处理。因为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与一般民事合同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不涉及外部第三人利益,处理两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就应当遵照一般契约原则,按照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来认定。如果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问题,则要遵循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尊重公司登记制度的公示效力。市场交易纷繁复杂,时间和效率是决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便利迅捷的交易方式是商主体追求效益的必要条件,要求交易双方在交易前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详尽调查对方的真实情况是不现实的,而且作为公司以外的第三方不可能如公司股东一般详细掌握公司的情况,如让善意第三方承担过于严格的甄别责任,则必然增加其交易成本,降低其交易积极性,交易不积极,资源不流动,则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在这种涉及公司外部的纠纷中,必须侧重保护外部第三人对登记内容乃至登记制度的信赖,故而也必须侧重保护基于这种信赖而发生的经济往来,因此工商登记在册的显名股东方是适格主体,而隐名股东是不适格的。
关于股东的定义,不同的语境、不同诉讼环境中有不同的内涵,如前所述,在内部纠纷中,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争夺的就是谁来享有股东投资权益,自然都可称为股东,但在对外诉讼中,基于外观主义原则,只有显名股东才是公司股东,在这个意义上说,隐名股东便不是公司股东。《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40条第22项就“股东”一词下定义之时,公司登记簿记载的股份持有人当然的视为公司的股东。《德国股份法》第67条第2款规定,“在与公司的关系中,只有在股票登记簿上登记的人,始得成为公司的股东。”我国公司法虽然没有对股东的定义下个明确界定,但在二十五条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股东的姓名或名称…”,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公司法条文上的股东的定义不应作扩大性解释,指的就是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表述跟公司法保持一致,没有采用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的表述,而用了实际出资人这一表述,从而与股东一词做了区别,从系统性解释看,这也表明公司法条文中的股东定义仅指显名股东。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法条的第三款规定的是隐名股东显名化的处理规则。那么,隐名股东显名化属于内部纠纷还是外部纠纷,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思路来处理?笔者认为,这纠纷实际上介于内外之间,因为这已超出了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小范围,且涉及到另一个利益主体即作为拟制法人的公司,股东显名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名字变更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在公司这个平台上进行,也必须以公司的名义进行。但公司毕竟只是个拟制人格,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所以隐名股东要显名化,其他股东的表态是至关重要的。与资合性较强的股份公司不同,有限责任公司更注重人合性,人合性的要求就是各股东之间要建立一种互相了解、友好信任的关系,否则将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巨大障碍。在股东隐名的情况下,除与该隐名股东相对应的显名股东外,公司的其他股东并不见得知晓隐名股东的存在,他所认同的合作伙伴是该显名股东,如果这些股东知晓自己的真正的合作伙伴是这位隐名股东,他完全有可能不允许其加入公司,或者自己不加入公司。从这点上看,这个纠纷虽然不属于外部纠纷,但是也带有外部纠纷的一些特征。隐名股东显名化的问题在性质上类似于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即都是涉及有关“新股东”的接受,因此司法解释确定的处理思路类似于股权转让,必须得到其他过半股东的同意。但显然不同于股权转让的是,股东不同意接受“新股东”的自然不需要购买该股权。
回到本案的语境中,公司解散诉讼,笔者认为也介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纠纷,涉及到股东的表态,涉及到公司的表态,从上论述可知,提起解散的适格主体只能是显名股东,即登记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上的股东,隐名股东不能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就诉讼策略而言,如果两原告作为隐名股东,先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或者提起显名化诉讼等方式,变成显名股东后再提起解散诉讼,或许不失为一个更佳途径。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个显名化诉讼也会存在一些有意思的情节,因为公司仅有两名在册显名股东,即本案中的两位第三人,两原告是隐名股东,假设剧情发展如本案一样,两位显名股东也缺席审理并不表态,法院将如何确定这两位显名股东的意思表示?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显名化须过半数方得通过。而且,两名原告还是香港居民,能否直接显名化登记在册,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承办人:郭宁华 余长勇 聂海琴
编写人: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郭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