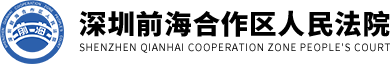前言
因为一个运输合同纠纷,两人对薄公堂,法官审理后却发现,这个案件并不简单,到底是什么引起了法官的重视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基本案情
原告吴某与被告姜某约定,吴某委托姜某将货物从香港进口至内地,由姜某负责安排运输、代为报关进口等,吴某按每公斤6元的价格支付费用。
2015年,吴某委托姜某运输一批货物,运费为8万元,吴某先支付运费4万元,约定货物到达之后再支付余款。姜某以某康公司的名义进口该批货物时,该批货物被海关以“申报不实,漏缴税款”为由查扣。在海关出具给某康公司的行政处罚告知单中显示,该批货物申报不实,漏缴税款人民币36万余元,海关部门对该公司行政罚款32万元。吴某向海关交纳了罚款32万元、补缴了税金36万余元,并重新委托其他报关公司报关进口,支付了报关费用16万余元、因为重新报关在香港产生的仓储费用5万元。
此后,吴某要求姜某对此进行赔偿。2017年,姜某向吴某出具了一份“协议书”,确认因自己报关出错使吴某的货物被海关查扣,造成吴某损失货值360万元人民币,经协商,姜某愿意赔偿吴某损失129万元。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赔偿款未果,遂诉至本院。
裁判结果
一、被告姜某退回原告运费人民币4万元及利息。
二、被告姜某承担原告吴某海关罚款、仓储费、二次报关费等损失的一半费用及利息。
裁判要点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姜某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双方形成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吴某、姜某达成协议,吴某只需支付8万元的费用,姜某即可帮助其完成运输、报关等一系列过程,将本应缴纳36万余元关税的商品运入深圳。 双方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逃避海关监管、不实申报、偷漏大额税款的目的,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应属于无效的合同。 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姜某应向吴某返还其收取的运费4万元。
同时,对于违法行为产生的损失,双方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在双方之间进行分担。被告在此后与原告达成了一份“协议书”,实际是双方对于偷漏税款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的分担的约定。对于违法行为的后果并非完全属于由当事人之间自行约定的范畴。从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立法本意来看,相应后果的负担应该使违法行为的双方均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取利益,这样才能达到既制裁已发生的违法行为,同时又树立行为标准,阻吓后来者的目的。如果对于后果的分担不但不能让一方受到惩罚,反而使其从中获益,显然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按照本案原、被告双方约定的结果,原告不但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代价,反而可以从中获得巨大收益,显然不合情理。该约定表面上属于双方对损失分担的约定,实际上是双方对于承担违法行为的后果的约定,亦属无效。
本案审理过程中,吴某明确其赔偿请求中包含了补缴的税款、罚款、仓储费用、运费以及二次报关的费用。但其补缴的税款36万余元,是其按照合法途径正常进口必然会发生的费用,是其将货物进口至深圳所应当承担的成本。上述费用不属于损失,不应由双方分担,而应由商品进口人即原告自行承担。其余因为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损失,可以双方之间分担。
被告作为进口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具有过错。本案所涉交易被告向原告约定收取的费用仅为8万元,但实际该批货物仅就应缴纳的关税就已经超过了36万元。原告作为长期从事进口商品的主体,从常识上来讲,不可能不知道被告提议的价格与按照正式途径从海关进口所应产生的成本的巨大差异。同时,本次交易并非是双方之间的首次交易,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双方在此前还有类似的交易,但因未被海关查扣,因而在双方之间未发生争议。在此情形下,如果说原告对于被告不实申报、偷漏税款的行为不知情,明显不合情理。即使原告在主观上没有积极的故意,也存在着放任、纵容被告偷逃税款的消极故意,而且原告还是偷逃税款的直接受益人。故原告对于本案所产生的后果亦有过错。
因此,吴某、姜某两者应当对于本案所涉违法行为的后果承担同等的过错责任。对于海关罚款、仓储费、二次报关费等损失,双方各承担一半费用。
结语
本案所涉及的“灰色清关”在实践中并不罕见,从业者应当摈弃侥幸心理,只有守法、诚信经营,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此类案件的合理处理有利于推动行业自律,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